
蟹会朗泮轩


独家抢先看
曾经做过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行政总厨的罗朗先生,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,做得一手好吃的中餐。这位热爱中国文化、对中国美食文化有着深刻理解的美国人,把他自己的餐厅开到广州沙面。

这是一幢百年老建筑,国民政府广播事业管理处的老办公楼,解放后一度是广州电台的办公室,现在做了一个广播博物馆,顶楼的阳台,就是朗泮轩。罗朗把朗泮轩打扮得古色古香,入门大堂,是一个如中药铺的茶馆,陈列存放着他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茶叶,这个地方,也是品下午茶的绝佳处。三个大小不一的房间,可供五十多人用餐,这估计已经是罗朗目前能服务的天花板了,所有的菜都是罗朗自己动手,只有一位助手,一顿饭,罗朗需要一周时间左右来准备。天台处,罗朗还辟出了一块菜地,做菜要用到的一些香料、花卉,就产自这一小块沃土。酷爱中华料理的罗朗,还在这里酿酒、做泡菜,而所有的老家具和餐具,也是罗朗掏来的,客人就餐时所用到的茶杯、碗、碟,可能是明朝,也可能是清朝,这是在与历史对话。

罗朗的菜,以中国二十四节气为主题,一个节气一个菜单,真正做到“不时不食”。当晚的菜单,以“立冬”为主题,都是这个季节的当季食物,比如螃蟹,不仅有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提到的“蟹酿橙”,居然还有“蟹会”:起锅烧油,放入切碎的干葱爆香,将清洗干净的花蛤放进去,待花蛤壳张开,汁水流出时加入一勺绍兴酒,盖上盖子,让蒸汽给花蛤加热7-8分钟后熄火,待冷却后手工取出蛤肉备用;将贝壳扔回锅中,加水,连同花蛤汁加盖煮30分种,滤出高汤;将蟹蒸熟,取出蟹肉备用,同样方式用蟹壳熬出蟹壳高汤;花蛤壳高汤和蟹壳高汤按1:1比例放入米中,作为高汤熬制成粥。粥熬好后,加入细葱碎和新鲜蟹肉制成米铺羹;取出的蛤蜊肉在贝壳内陈列出漂亮的扇形,下方放置海盐,加入新鲜莳萝叶和莳萝油,再配以葱花饼,一碗蟹肉米铺羹、一扇花蛤肉、一团葱花饼,三者一起就是“蟹会”。吃的时候将贝壳里的所有东西倒进米铺羹,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吃了。这个菜,鲜得令人咋舌,近似于香芹味道的莳萝,有着更强烈的清凉味,温和而不刺激,味道辛香甘甜,盖住了花蛤和螃蟹的腥味,又不夺它们的鲜味,给这道菜画龙点睛,十分出彩。

罗朗给这道菜做了一张精致的卡片,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:明末清初,社会更迭,社会阶层发生了改变,涌现不少挥金如土的“暴发户”,在传统的世俗眼中看来,这是一群只懂花钱却不懂分辩事物好坏的无知之徒,毫无尊贵可言。出自书香门第的张岱,家中财力雄厚,生活主要就是吃喝玩乐,到处游玩,并顺便写写文章。像张岱这类的传统贵族,几乎人人都是美食家,不仅能吃得起山珍海味,也有一套吃法的讲究及评判食物优劣的标准,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懂生活。张岱有许多文章流传于世,在他四十多岁时,经历了朝代的更迭,笔下的内容也在变。他曾在文章中记载深秋时节蟹的鲜美肥嫩,又不禁因生活过于奢靡发出“酒醉饭饱,惭愧惭愧”的感慨。

原来,罗朗这道菜,创作灵感来自于张岱的“蟹会”。张岱是明清之际的史学家、文学家,浙江绍兴人,祖籍四川绵竹,故又自称“蜀人”。张岱出身仕宦家庭,祖上四代为官,高祖父张元汴是明隆庆五年的状元,也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,家声显赫。张岱生来如众星拱月,锦衣玉食,数十号奴仆围着他转,紧张地盯着他的表情,“喜则各欣然,怒则长戚戚。”他太会玩,也太会写,既有纨绔子弟的奢豪之举,也有晚明名士文人的狂狷之性。但是,你还不得不佩服这个张岱,经史子集,无不通晓;天文地理,靡不涉猎。他在《自为墓志铭》中列出著作十五种,之后又还有诗集、文集、杂剧、传奇等作品。其中《夜航船》一书,内容有如百科全书,包罗万象,共计二十大类,四千多条目。他的著述之丰,用力之勤,令人惊叹不已,这也使得他与一般纨绔、风流名士彻底区别开来。大散文家、大诗人、小品圣手等名誉之外,他还是顶级的美食家,他在《陶庵梦忆》中有一篇“蟹会”,这样描述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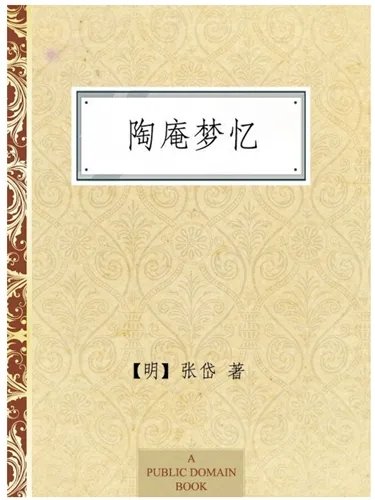
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,为蚶,为河蟹。河蟹至十月与稻梁俱肥,壳如盘大,坟起,而紫螯巨如拳,小脚肉出,油油如螾蜓。掀其壳,膏腻堆积,如玉脂珀屑,团结不散,甘腴虽八珍不及。一到十月,余与友人兄弟辈立蟹会,期于午后至,煮蟹食之,人六只,恐冷腥,迭番煮之。从以肥腊鸭、牛乳酪。醉蚶如琥珀,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。果蓏以谢橘、以风栗、以风菱。饮以玉壶冰,蔬以兵坑笋,饭以新余杭白,漱以兰雪茶。由今思之,真如天厨仙供!酒醉饭饱,惭愧惭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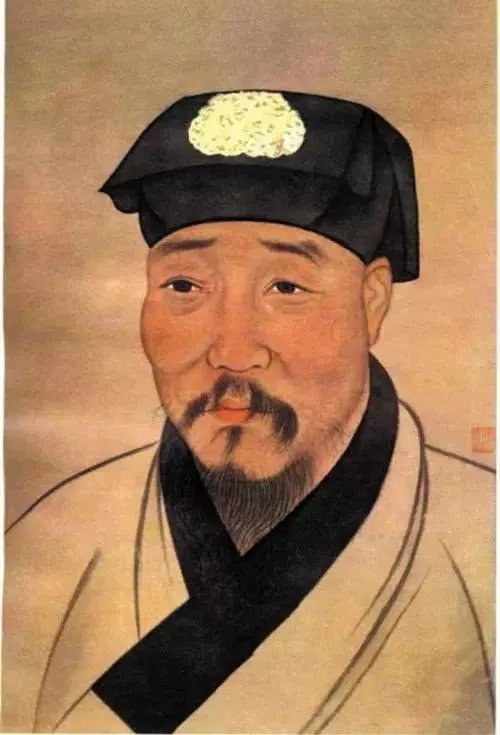
这段文字不难理解,首先蟹的品质得有保证,数量也不能少,一人六只,怕冷腥必须分批煮。单吃蟹那是不行的,必须搭配肥腊鸭和牛乳酪,饮料要上玉壶冰,蔬菜必须是兵坑笋,米饭佐以新余杭白,最后用兰雪茶漱口。张岱写下这段文字时,明朝已经灭亡,他舍弃故园,带着残稿,携着破琴残砚,带着孩子,披发遁入深山,自当野人,过上了颠沛流离,衣食无着的遗民生活,这段回忆文章,估计是在望梅止渴。他享受了繁华,也阅尽了沧凉,在恶劣的环境下写出巨著《石匮书》,时人评价:“当今史学,无逾陶庵”。对旧时奢华生活,张岱终归过意不去,所以最后写了“惭愧惭愧”!

罗朗懂张岱,这个菜以“蟹会”命名,而且,就用张岱的说法,“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,为蚶,为河蟹。”来了个蚶和蟹的组合,而且,把香料之王莳萝加了进来,一点都不唐突。这个号称洋茴香的香料,在张岱之前就被广泛运用。晋代裴渊在记录广州特色的《广州记》说莳萝“生波斯国。马芹子色黑而重,莳萝子色褐而轻,以此为别。善滋食味,多食无损。”南宋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的104道菜谱里,记录了两道应用莳萝的菜:玉灌肺和满山香。可以说,中餐用莳萝调味,历史悠久,可惜我们中餐现在很少用到莳萝。罗朗这个美国人,比我们还懂中国。

吃罗朗的菜,不仅仅是在与食物对话,更是与历史对话,与文化对话。美食的鉴赏,我们常说的“色、香、味俱佳”,这只是视觉、嗅觉、味觉的体验,罗朗把美食直接拉进历史,装上文化,这样的一顿盛宴,已不是传统美食欣赏可以读懂,需要静下心来,听听罗朗的絮叨,细细回味。

罗朗的其他菜,也如“蟹会”,背后有他的创作逻辑和故事。感谢罗朗,让中华美食高贵起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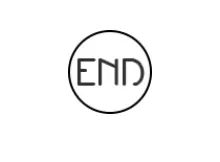
“特别声明:以上作品内容(包括在内的视频、图片或音频)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“大风号”用户上传并发布,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。
Notice: The content above (including the videos,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)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,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.”




